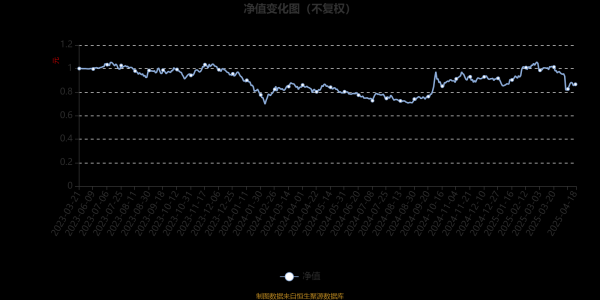2025年是叶挺诞辰129周年配资平台佣金,是叶挺独立团建团100周年。
1925年11月,叶挺独立团在肇庆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指挥的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屡破强敌,屡建奇功,为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铁军”荣誉,团长叶挺因战功卓著,被誉为“北伐名将”。
当前,史学界对叶挺独立团北伐首战发生地只有个别学者进行了初步探讨,对曹渊参加叶挺独立团的时间和地点等史实则至今无人专门研究。笔者通过史料分析,认为叶挺独立团北伐首战是攸县战役,战斗发生在渌田与黄茅铺之间,并以占领攸县县城为标志;关于“铁军”盾牌背面的题词内容,认为应以《第四军纪实》的记述为准;关于曹渊参加叶挺独立团的时间地点,提出曹渊1926年5月在广州参加叶挺独立团的观点更符合历史事实。
关于叶挺独立团若干史实的考证
叶挺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指挥的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其前身是1924年11月成立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1925年11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旅扩编为第十二师时,在广东肇庆成立,始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全团官兵2000多人,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1926年初,第十二师进行整编,第三十四团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仍为团长,通常称“叶挺独立团”。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文史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通过实地调研、专访、研讨和编纂出版著作等方式,对叶挺独立团的历史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出版、发表了大量与叶挺独立团有关的著作和文章,充分肯定这支武装在中共党史和军史的重要地位,及其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笔者在研究叶挺独立团历史时发现,已编纂出版的有关该团历史资料和相关著作、文章,有关史实方面进行考证的只有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叶挺独立团史料研究》和刊载在《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四期的《叶挺独立团成立时间的考证》、《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五期的《北伐战争中“铁军”称号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一期的《叶挺独立团北伐出发入湘时间考》等几篇(部)。史学界对叶挺独立团北伐首战发生地只有个别学者进行了初步探讨;对曹渊参加叶挺独立团的时间和地点等史实则至今无人专门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历史事实出发,在掌握有关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比较和研究,对上述三个史实提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看法,以实事求是精神,还原历史真相。
一
对叶挺独立团北伐首战发生地的考证
笔者从所接触到的历史资料和书刊中发现,史学界对叶挺独立团出征北伐第一战发生地存在三种不同说法:一是认为第一次战斗发生在汝城;二是认为在安仁渌田打响北伐首战;三是认为北伐首战应在攸县。下面,笔者就所掌握的资料对这三种说法逐一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北伐首战在汝城的说法
这一说法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中山大学《叶挺》编写组编写、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叶挺》一书。该书对叶挺独立团北伐首战作如下记述:“叶挺独立团到达汝城附近,最先和谢文炳千余人发生战斗,经一夜激战,敌被击溃,残部向东北方向逃遁,独立团旗开得胜,占领了汝城”。由中共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北伐先锋》,萧健玲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叶挺独立团团史》等著作也持这一说法,对叶挺独立团在汝城的战斗记述也与《叶挺》一书的记述大同小异。
这一说法由于出现较早,引用者也较多,故有一定的影响。经考证,叶挺独立团北伐时并没有经过汝城,更未在汝城发生过战斗。依据如下:
史料一:叶挺独立团北伐行军作战时使用的《湖南邮路全图》所描绘的线路走向证实,叶挺独立团北伐没有经过汝城。图1是叶挺的同学、独立团团部军需处主任兼辎重队会计长陈卓立亲手所绘并保存,1959年捐献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藏有复印件)。该图用红线和红色箭头描绘并标注有独立团进军湖南、湖北两省经过的地方,沿途经过宜章、郴县、永兴、安仁、攸县、醴陵、浏阳、平江、通城、中伙铺等地,就是没有提及“汝城”(陈卓立绘:《湖南邮路全图》)。

图1:陈卓立绘:《湖南邮路全图》
史料二:叶挺独立团职员寄自湘南前线的函件。该函件分别于1926年的6月23日在《广州民国日报》、6月30日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详细记述叶挺独立团从韶关出发到达湖南安仁前线的每天行程:“二十日下午六时始抵韶州(今韶关)……二十四日由乐昌至九峰墟……二十五日经蔚岭而至山顶,上有一关口,上书有‘蔚岭南’三字(是光绪十八年所建的),过了此大山到塘村。二十六日由塘抵良田……二十七日,由良田开抵柳(郴)州……是日彬(郴)县长及商会均宰猪及绍兴酒以犒本军。二十九日在(郴)县东门外开军民联欢大会……三十日彬(郴)州开抵五里牌。三十一日由五里牌抵永兴县城,各铺户均插欢迎旗……六月一日由永兴抵龙海塘墟,计是日足行百余里,亦可谓辛苦之极。二日由龙海塘抵安仁县城……三日暂留安仁以侦察战地,及使官兵得以小休……敌人知我军已到达,乘本军疲于路程,本日午间即与敌接触……”
写这封信的职员清楚地描述了叶挺独立团的行军路线和时间,没有到过汝城县城或近郊的记述,在6月2日前也未遇到过任何敌军,更没有在汝城打仗的任何记述。这行军路线和时间,也与陈卓立绘的叶挺独立团进军路线图高度吻合。
至于《叶挺》《北伐先锋》等著作记述叶挺独立团在汝城“旗开得胜,占领了汝城”的原因,笔者在研究叶挺独立团有关史料时发现,这些著作的记述,均与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邓演存、林一元等10多名老兵1965年写的回忆录《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加北伐战争的回忆》所描述的叶挺独立团在汝城作战的内容相差无几。该份回忆资料是这样写的:“一九二六年五月间,独立团首先由粤入湘为北伐前锋。进入湖南汝城时,在共产党组织的侦探队和响导队、狙击队的协助下,最先和谢文炳一部敌军约千余人发生战斗,乘夜冒雨进攻,迅速夺取汝城西南高地,经一夜激战,将敌人击溃,残敌向东北方面逃遁,遂即占领汝城,旗开得胜。”这是笔者发现的最早记述叶挺独立团在汝城作战的史料。后来记述叶挺独立团在汝城作战的著作或文章均与该史料的描述内容大致相同。据此推断,这些著作或文章记述叶挺独立团在汝城作战的内容均源于邓演存、林一元等人的回忆。这些人的回忆是在叶挺独立团北伐入湘作战约40年之后的1965年,且这些回忆者没有随叶挺独立团先遣入湘,而是在叶挺独立团湘南首战结束后,随第四军其他部队入湘参加北伐战争的,并非事件的亲历者。而事件亲历者、率部从广东韶关到湖南安仁的独立团团长叶挺写的《叶挺同志参战报告》和参谋长周士第的回忆录,都没有到过汝城和在汝城与敌作战的任何记录。为此,笔者认为:邓演存、林一元等人的回忆史实有误。
根据上述史料分析,笔者做出如下判断:叶挺独立团没有在汝城与敌人发生过战斗,北伐首战不是在汝城。
(二)北伐首战在“安仁渌田”的说法
这一说法的最早起源应是叶挺1926年9月9日写的《叶挺同志参战报告》,刊载在《中央政治通讯》1926年第3期上。该报告称:“独立团于五月二十日奉命由广东入湘……五(六)月三日第一次在安仁渌田之役虽将敌击退,但损失步枪三十余支……”其次为云今写的《第四军北伐作战经过》,刊载在1927年1月出版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追悼阵亡将士大会特刊》上。该文称:“……一、安仁渌田之役。是役乃我北伐军第一次与直系军阀的接触,同时也是本军北伐光荣历史上的第一段……”此后出版的有关史料和著作,有的直接引用上述说法,如第四军纪实编纂委员会编写、文海出版社1948年出版的《第四军纪实》,称叶挺独立团首战为“安仁渌田之役”。有的稍有改动,如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叶挺独立团团史》称:“叶挺独立团安仁渌田、黄茅铺之战……获得了首战湘南的重大胜利。”这些说法虽略有不同,但均可归类为“安仁渌田”的战斗为叶挺独立团北伐首战的说法。
该说法因源于叶挺写的《叶挺同志参战报告》,故较为流行。但根据史料分析,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是不够准确和科学的。理由是:安仁是一个县,而渌田是攸县属下的一个乡镇,民国初年至今都属攸县管辖,故两者不能并列。叶挺的参战报告中称首战为“安仁渌田之役”应是笔误,其他史料或著作、文章也是受此影响而使用这一说法。
(三)北伐首战在攸县的说法
这一说法也较流行。原叶挺独立团战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韩伟在1985年10月回忆道:“我团在攸县的战斗打响了北伐的第一枪,这一仗打败了强敌,占领了攸县县城。”周士第在其回忆录中,称“渌田战斗的胜利是初战大捷”。渌田是攸县下辖的一个乡镇,故这一说法与韩伟的回忆“我团在攸县的战斗打响了北伐的第一枪”并不矛盾。禤倩红编写的《叶挺生平活动简表》也作同样的记述:“在叶挺率领下,独立团乘胜占领攸县,取得首战胜利。”
笔者认为,称叶挺独立团北伐“首战攸县”或“攸县战役”这一说法准确。理由如下:其一,这一说法符合历史事实。叶挺独立团6月2日到达安仁县城。6月3日上午,开赴攸县的渌田、安仁的龙家湾前线,打响了北伐战争第一枪。4日,叶挺独立团取得渌田战役的胜利,阻止了敌谢文炳、唐福山部攻占安仁、耒阳的企图。在叶挺独立团的猛烈打击下,谢、唐放弃攸县县城。5日下午,叶挺独立团占领攸县县城,取得北伐战争的第一个大捷。这里之所以表述为叶挺独立团首战攸县,并没有提首战安仁,其一,是因为攸县全境被北洋军阀吴佩孚属下的谢文炳、唐福山部占领,而当时湘南的安仁、汝城、郴县等县还在唐生智部控制中,叶挺独立团作战的主要目的是阻击北洋军阀攻占湘南、守住安仁、攻打攸县,实施北伐,所以这一说法符合历史事实。其二,以主战场攸县命名为叶挺独立团北伐首战攸县或攸县战役符合历史惯例。该战役的主战场是攸县南部渌田镇渌田村。次战场有两个:一个是在渌田镇的江口村,另一个是在安仁县龙家湾的黄茅铺。称叶挺独立团北伐首战攸县或攸县战役,以最终攻占攸县县城为胜利的标志,这符合历史惯例,也与醴陵战役、平江战役、武昌战役一脉相承,提法规范,更容易让人知晓。这一说法并没有否认安仁龙家湾次战场的作用和地位,更不否认安仁县作为此次战役指挥地、后勤补给地的重要作用,而是范围更广了。这一战役包括了渌田、龙家湾之役和攻占攸县县城以及后面在攸县范围内所有的大小战斗。
二
对“铁军”盾牌背面题词内容的考证
1927年1月15日,武汉粤侨联谊社向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赠送“铁军”盾牌,以表彰其在北伐战争中的丰功伟绩。叶挺代表第四军接受这块盾牌。该盾牌高1米、宽半米、重达数十斤。正面嵌着“铁军”两个大字,上款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体同志伟鉴”,下款为“民国十六年一月十五日武汉粤侨联谊社同人敬赠”。背面刻有四言题词。令人感到惋惜的是,这块盾牌如今下落不明。关于这四言题词内容的记述,笔者通过多方查找有关史料,只在《第四军纪实》一书中发现该盾牌的正面照片,但背面照片书中没有收录,只收录题词的内容。目前也没有发现记述盾牌背面题词内容的当时史料。
由于没有照片和其他原始资料佐证,经过近百年的历史变迁,“铁军”盾牌背面的四言题词内容,也衍生出多种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的四言题词,大体可分如下三类:
其一,该书对“铁军”盾牌四言题词作如下记述:“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振迩遐。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担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马,愿寿如铁,垂亿万年。”这是笔者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关于盾牌四言题词的记述。邓演存、林一元等12名原第四军老战士1965年写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加北伐战争的回忆》,关于“铁军”盾牌四言题词的记述是:“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振迩遐。能守纪律,能无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功用若铁,人民倚马,愿寿如铁,垂亿万年。”这些老战士的回忆,与《第四军纪实》的记述,除将“能毋”改为“能无”,并缺“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担负,如铁之肩”四句外,其他完全一致。早期的专家学者,在记述这段内容时,也大多使用与《第四军纪实》的记述完全一致的内容。如198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曾成贵、江抗美著《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1987年出版的《近代史研究》第五期刊登陈立平撰写的《北伐战争中“铁军”称号的考证》等,记述的“铁军”盾牌四言题词内容与《第四军纪实》的记述也完全一致。
其二,如曾参加北伐战争的国防部原副部长萧克在《铁军纵横谈》中回忆道:铁盾背后有一首四言题词,全文是:“烈士之血,主义之花,4军伟绩,威振迩遐。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摧峰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担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亿万年。”与《第四军纪实》的记述作比对,“4军”“摧峰”应为“四军”“摧锋”之笔误,但把“倚马”改为“倚焉”,使四言题词开始出现差异。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张发奎口述自传》,把《第四军纪实》的“担负”改为“负担”、“之肩”改为“在肩”、“倚马”改为“倚焉”,其他没有变化。张发奎作为北伐当事人,他的口述自传之所以与《第四军纪实》的记述出现较多的差异,是因为该书初稿原为英文,后翻译成中文,个别字词的翻译难免与中文原意有所不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叶挺独立团史料研究》在收录四言题词时,除了将“倚马”改为“倚焉”外,其他与《第四军纪实》的记述无异,这也可能是该书作者抄录萧克将军的回忆资料而造成的。
其三,如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叶挺将军传》记述的“铁军”盾牌四言题词为:“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振迩遐。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抱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忆万年。”这一记述,除把“担负”“倚马”“垂亿”,分别改为“抱负”“倚焉”“垂忆”外,其他均与原《第四军纪实》记述的内容一致。这是笔者发现的最早把原《第四军纪实》记述内容的三个词都进行了修改,但又没有注明出处的版本。此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卢权、禤倩红著的《叶挺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共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编写的《北伐先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萧健玲著的《叶挺独立团团史》等著作和相当部分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章,以及部分纪念场馆、网站,新仿制的“铁军”盾牌等,记述的四言题词的内容均与《叶挺将军传》记述内容完全一致。个别著作还对四言题词的出处做出注释,如《叶挺独立团团史》注明为摘自1948年编写的《第四军纪实》,但又没有完全按原文抄录。
对照上述三个类型“铁军”盾牌四言题词内容,不难看出,第一类型形成时间最早,且是历史当事人的记(忆)述,可信度更高。后面的两个类型是由第一类,也就是最早的版本——1948年编印的《第四军纪实》四言题词衍生而来。之所以有第二种类型的版本,是忆述者因相隔年份较久而回忆有误,或使用时一时笔误等造成。之所以衍生出第三种类型的版本,具体原因无法考究,但可推测其原因如下:认为“革命担负”之“担负”与“革命”组合在一起不符合后来常用的“革命抱负”的习惯称谓,故改之。将“倚马”改为“倚焉”是因该题词前3句排第8与16位的字都押韵,若第4句排第8的字为“马”字,则与本句排第16的“年”字不押韵。为此,使用者推断《第四军纪实》排版时错将“焉”排成“马”,故使用时为了押韵的需要,把“马”改为“焉”。“垂亿”二字,其中“垂”为“传下去、传留后世”之意,“亿”是形容很多的数字,“垂亿万年”可理解为“将铁军精神流传千秋万代”。而“垂忆”意为“传留后世的思念和回想”,这与“铁军”盾牌四言题词所宣扬的铁军精神解释不通。至于使用者为何把“垂亿”改为“垂忆”,不得而知。
笔者认为,《第四军纪实》四言题词中的“担负”,意为“肩挑背负”,可引申为“承受、肩负革命的重任”,在此使用“担负”一词是可以的;“人民倚马”之“倚马”,意为“以马为依靠、倚靠”,引申为“‘铁军’是人民的依靠、人民的靠山,是保护人民的部队”,也可以在此使用。至于为了押韵,把“马”改成“焉”,则为笔者所不认同。
三
对曹渊参加叶挺独立团时间地点的考证
笔者在查阅叶挺独立团有关史料和著作时发现,对曹渊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的时间地点存在两种不同的记述:一种认为,曹渊是1926年1月后在肇庆参加叶挺独立团的。如《北伐先锋》记载:“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序列表(1926年1月—1926年12月)团长:叶挺……参谋长:周士第第一营营长:曹渊卢德铭(后)……”《叶挺独立团团史》里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序列表(1926年1月—1926年12月)”也作了同样的记述。《叶挺独立团史料研究》则作如下记述:“周士第任参谋长后(参谋长先是吴济民,两个月脱离,由周继任)又从黄埔军校调来共产党员曹渊(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任第一营营长。”这一记述表达的意思是:周士第在叶挺独立团成立两个月后(即1926年1月)调任参谋长,曹渊从黄埔军校调来接替周士第任第一营营长。这一记述对曹渊参加叶挺独立团时间地点的表述虽与上述两书表述的方式和角度不同,但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即认为曹渊是1926年1月后在肇庆参加叶挺独立团的。另一种认为曹渊是1926年5月在广州参加叶挺独立团的。笔者通过对史料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考证,认为后者的观点符合历史事实。主要依据是:
史料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追悼阵亡将士大会特刊》对曹渊烈士生平的记述:“曹烈士名渊,字溥泉,安徽寿县人……十三年(1924年)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招考沪上,君应考获取……(1925年)十月二次东征,追敌至河婆……师抵潮汕,调任第三师九团一营营长。十五年(1926年)三月因老亲函召,请假回里省亲。后见国民政府已定北伐计划,复来粤,任第四军独立团第一营营长,旋即出发……”从上述史料可知,曹渊在第二次东征抵达潮汕后(1925年底)至1926年3月间,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九团一营任营长。1926年3月请假回乡探亲,后获悉国民政府准备北伐的计划后才回到广东。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从广东到其家乡安徽寿县,再回到广东,最快也要一个多月,因而曹渊回到广东时应在四五月间。期间,叶挺独立团仍在肇庆、新会驻防,曹渊是不可能在此期间加入叶挺独立团的。
史料二:周士第在《叶挺同志革命斗争片断》写道:“党支部设六个党小组,第一营小组长先是周士第担任,后来周士第调到团部,第一营营长由曹渊担任,并由曹渊任党小组组长。”从周士第的回忆可知,第一营营长和党小组组长开始时由周士第担任,他调任团参谋长后才由曹渊接任第一营营长和党小组组长,但没有说明周士第调任团参谋长、曹渊接任第一营营长的具体时间地点。
史料三:曾任高要第二区农民协会领导人许其忠1964年回忆道:“我于七日(1926年1月7日)与佐洲等往府衙门三十四团团部,见了团长叶挺(肇庆防军独立团的前身),报告地主残杀农民事情,请他派兵援救。他即答应派第一营前往领村,并叫我和周士第营长面谈出发时间。”《叶挺独立团团史》记述:“8日,叶挺派出独立团第一营之第二、三两个连及营部官兵共276人,由周士第率领……10日上午到伍村,中午抵达领村,开始调停工作。”“1月13日晨,率部返回肇庆……向叶挺汇报领村调停情况和请示具体任务,当日开赴江门、新会,帮助开展农会活动。”由此可见,率部前往领村解决事端的第一营营长是周士第,不是曹渊。第一营奉命开赴江门、新会时,营长仍是周士第。
史料四:周士第撰写的《曹渊同志事略》,对曹渊就任第一营营长的时间、地点和情景作清晰的描述:“中国共产党决定出师北伐,并决定派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先遣队,一九二六年五月初由广东省肇庆、新会出发,向湘南进军。又决定增派几个党员到独立团工作,以增强党的领导,曹渊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党决定曹渊同志任第一营营长。此时,第一营由新会开到广州市,住在黄沙车站附近,准备乘火车开赴韶关。曹渊到时,大家对他很亲热……”
史料五:据曹渊烈士儿子曹云屏忆述:“叶挺独立团出发北伐前夕,在广州城内司后街叶家祠,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干部会……父亲随同周恩来一起到了叶家祠,并宣布原第一营营长周士第调任参谋长,由父亲接任了第一营营长。”曹云屏的忆述,除印证周士第对曹渊到独立团担任第一营营长的时间、地点的回忆是准确的外,还说明了周士第是1926年5月才在广州卸任独立团第一营营长职务的。
通过对上述史料的分析,1926年5月前曹渊的革命历程是清晰可见的:1924年11月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担任校本部直属新军第一团学兵连党代表。1925年6月,任党军第一军一旅一团三营八连连长,同年10月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1925年12月至1926年3月,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九团第一营任营长。1926年3月中旬回安徽寿县探亲,5月回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第一营营长,之后踏上北伐的征程。
综上所述,我们对叶挺独立团上述三个史实得出如下考证意见:(1)叶挺独立团北伐首战是攸县战役,战斗发生在渌田与黄茅铺之间,并以占领攸县县城为标志。(2)“铁军”盾牌背面的题词,应以《第四军纪实》的记述为准,即:“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振迩遐。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担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马,愿寿如铁,垂亿万年。”(3)曹渊不是1926年1月后在肇庆参加叶挺独立团的,而是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离开肇庆、新会,在广州集结时参加叶挺独立团的。
对叶挺独立团上述史实的考证意见,只是笔者的一点管见,供学界探讨。
作者:陈灿和,广东省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二级调研员;韦相伍配资平台佣金,广东省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四级调研员。
淘配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